一卷在手,饥可充肠,寒可御冷,独处可作良伴,郁悒可解烦忧。书籍,这无声的智者,虽未必能让人立竿见影地增长才干,却也能在潜移默化中为精神寻觅到静默的庇护所,使心灵获得抚慰,令人生平添几许雅趣。

我除了上学之外,业余看书生涯,始于十岁。那时,我踮着脚尖从祖母的书架上抽出一本《三字经》,虽然只认得几个字,也不解其意,但那油墨的清香与纸页的触感,已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热爱阅读的种子。渐渐地,我学会了在书中寻找快乐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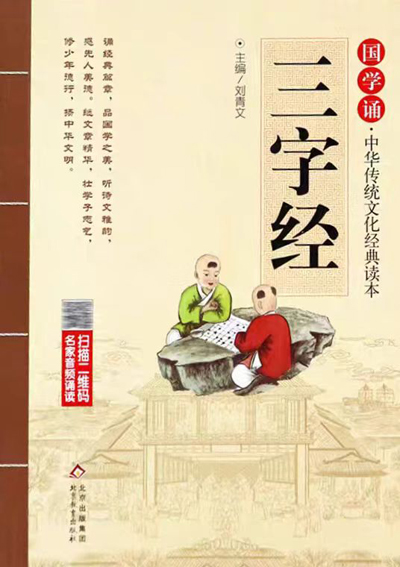
初中时期,《西游记》里孙悟空的火眼金睛,《水浒传》中梁山好汉的江湖豪情,《三国演义》里诸葛亮的足智多谋,《红楼梦》中黛玉葬花的凄美,都成为童年最鲜活的记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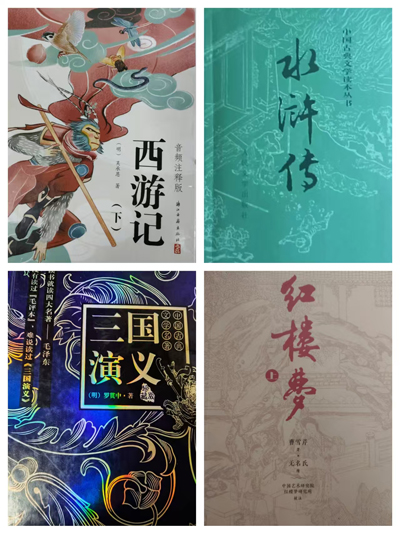
《诗经》里的“梧桐生矣,于彼朝阳”、“萚兮萚兮,风其吹女”等唯美诗句,让我从小就触摸到《诗经》里的诗心风雅,也让我在梧桐树下感受到生命最初的悸动。摇曳的叶影与斑驳的光点,仿佛都在应和着千年前的诗行。而那本李清照的《漱玉词》,则让我在《声声慢·寻寻觅觅》中“梧桐更兼细雨,到黄昏、点点滴滴”的婉约词句里,触摸到了宋代才女的细腻情感。时至今日,我仍记得在院子的梧桐树下捧着《漱玉词》,书中《声声慢》的句子与窗外淅沥的雨声交织,屋檐滴落的雨珠在地上溅起水花,仿佛也在应和着这位宋代才女笔下的凄美意境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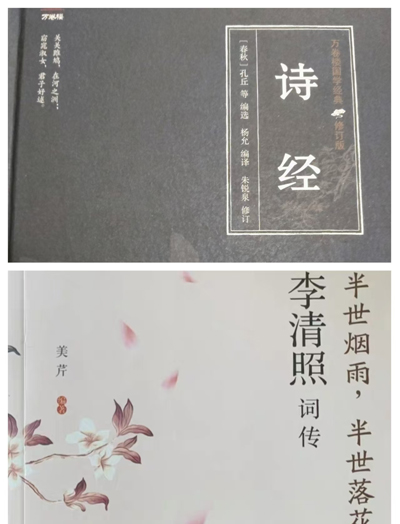
祖母是位虔诚的传统文化守护者,她经常在书房里观书着墨,墨香氤氲中,她总说:“字见风骨,落笔生情。”那些年,我有时候也写一些简单的文章,但她总说我写得不够婉转,也缺少力度。书房里那几套《尚书》、《周易》、《论语》、《礼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古文观止》、《东周列国志》等其它一些破旧的古代书籍,是我那个时期的精神食粮。记得第一次读到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时,胸中涌起莫名的激动,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,竟让我这个执着的少年热血沸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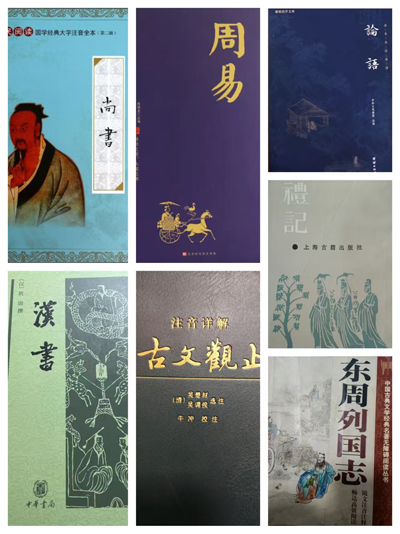
高中时期的寒暑假,我像只勤劳的小蜜蜂,勤翻家中的旧书,从《楚辞》、《春秋》到《史记》,再从《陶渊明集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到《苏轼文集》,每一本书都被我视为珍宝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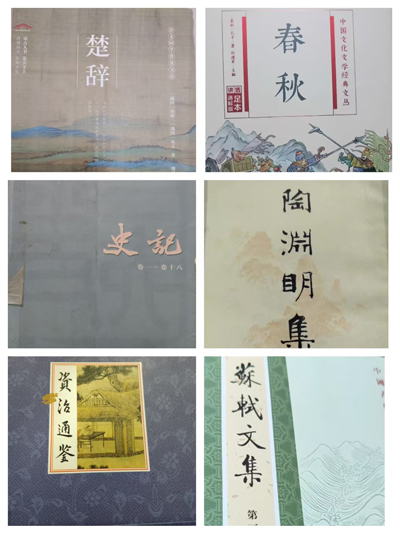
“读书明智”四字,道尽典籍真谛,那些穿越千百年的文字,既是滋养心灵的甘露,又是照见自我的明镜。在古典文学的长河里,我们不仅触摸到先贤的智慧,更在字里行间获得精神的滋养与人生的启迪。庄子的逍遥思想,让我在尘世纷扰中寻得了一片精神自由天地。韩愈笔下的雄文华章,让我感受到“文起八代之衰”的慷慨气魄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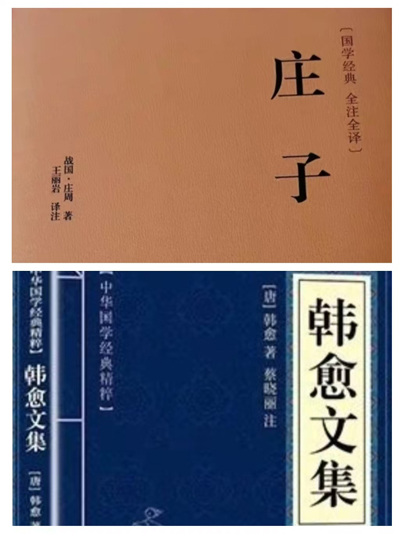
那个年代,看书对我而言,是种多层次的享受。那一本本书籍宛如汩汩清泉,能够涤荡心灵的尘埃;又似习习凉风,驱散暑气带来的烦躁。在书里,我领略到了诗人的细腻情思,也感受到祖父当年寒窗苦读的风范。每一本书好像都是一个新世界,翻开扉页的刹那,如同踏上了一场穿越时空的旅行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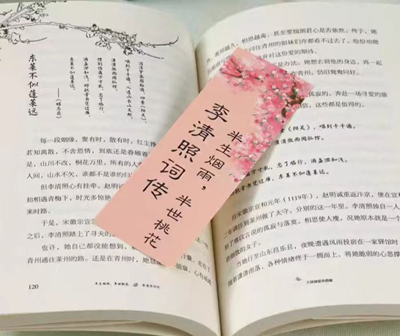
如今,每当我回老家翻开那些书页,总能闻到童年书房里特有的墨香,仿佛看见祖母在灯下批注的身影,还有那依桐听雨的遗韵,在这个数字化阅读日益盛行的时代,我依然珍视纸质书籍带来的独特体验,那手指摩挲书页的质感,和眼睛追逐铅字时的专注,以及合上书页时那份满足与宁静。书籍,不仅是知识的载体,更是文化的传承。

从连环画册到古典经籍,从懵懂孩童到知非之年,书籍始终是我忠实的朋友。它们让我领略“先帝知臣谨慎,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。受命以来,夙夜忧叹,恐托付不效,以伤先帝之明”的躹躬尽瘁,也让我感怀“花自飘零水自流。一种相思,两处闲愁。此情无计可消除,才下眉头,却上心头”的缠绵悱恻。那些泛黄的书籍,陪伴我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。在书香的浸润中,我永远不会忘记祖母的启蒙与教诲;也不会忘记有一位老师,她曾是我砚台旁的一盏明灯,如桐下雨韵,化作墨池涟漪,滋养我笔底烟霞,永远激励着我的前行!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