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的这个暑假,我在老家住了一段时间。三楼的一间书房,是我每天必到的地方。祖父曾经说,这里的书大半是曾祖母留下的,小部分是他添置的,(而父亲买的书,都放在另外一个城市的书房里。)记得上小学之前,我总爱翻有插画的本子,遇到生字便跳过去,是祖父握着我的手,让我在“学而时习之”这里朗读,从此,书页间的墨香便缠住了我的脚步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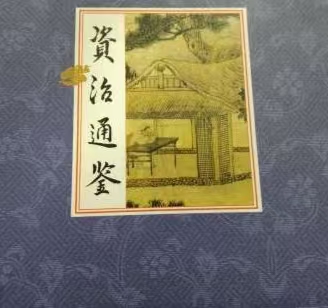
父亲常提起他童年的夏天:没有空调的屋子里,只有落地电风扇摇着头吹散暑气,他有时也在院中的树下,听着蝉鸣读《古文观止》。这次他送我回老家时,拍了拍我的肩:“体验故乡的生活,读读圣贤的书经,比在市区有意思。”于是那段时间,我抱着作业本走上三楼,在这些古老的书籍里,寻找“书中自有黄金屋”的乐趣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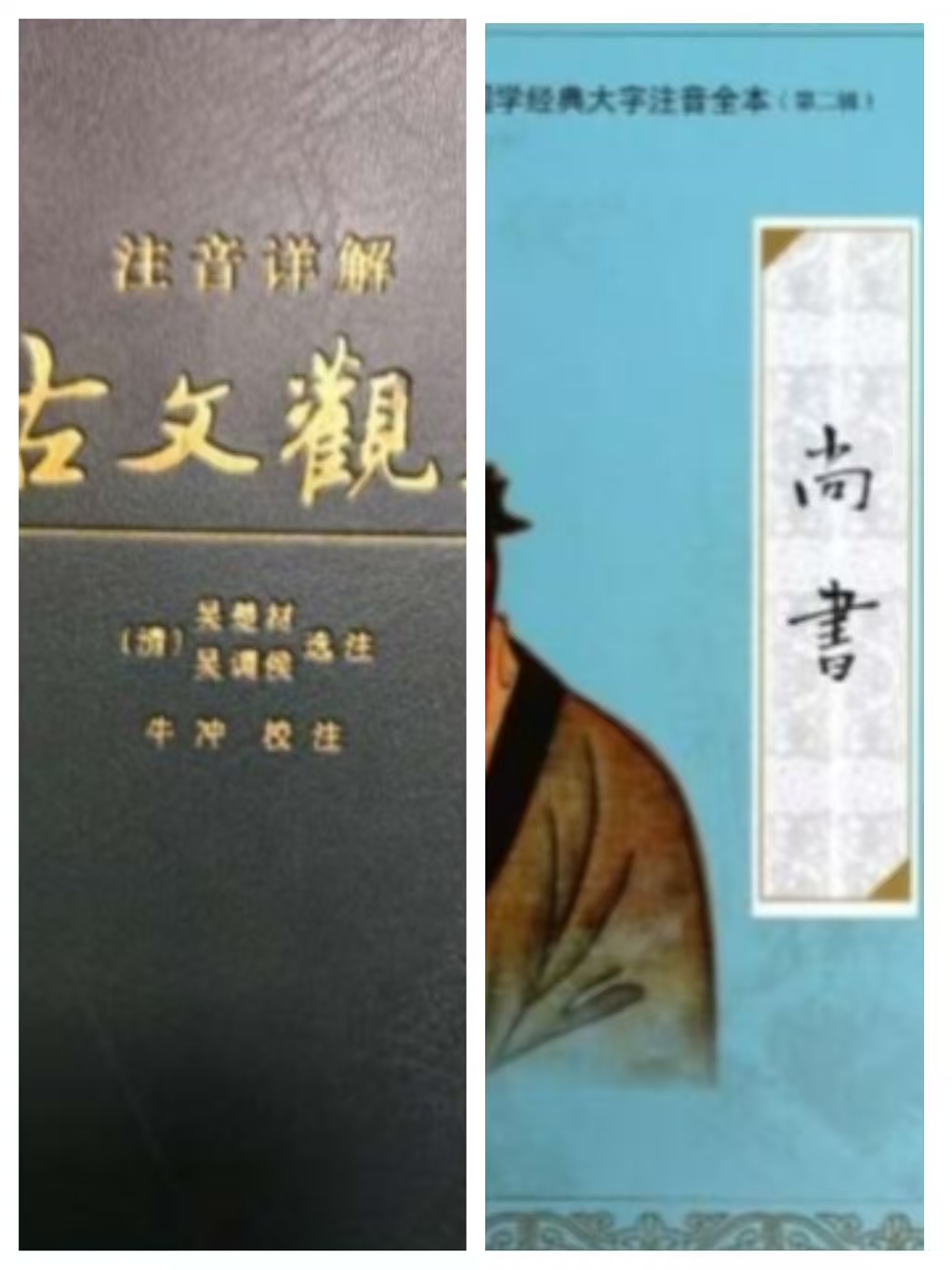
曾祖母和祖父留下的书柜像座小山,《楚辞》的这本躺在最上层,《古文观止》的页面也已很旧,《史记》的书册间还留着曾祖母翻过的书签。我总先翻《楚辞》,读到“路漫漫其修远兮,吾将上下而求索”时,会望向远处的小溪——两千年前屈原的江水或许也这般清澈。父亲让我每天写篇作文,再试着用文言改写,并要求我半天写成。我捧着《资治通鉴》里的“兼听则明,偏信则暗”挠头,笔尖在稿纸上乱打草稿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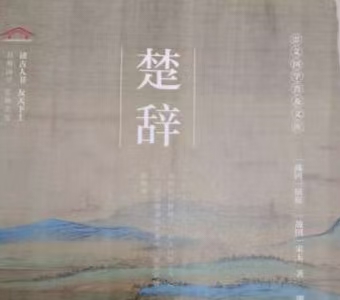
有一天,翻到《前赤壁赋》,正巧窗外暴雨大作。雨点砸在院子上,像千万根银线敲打芭蕉叶,我忽然联想起了“寄蜉蝣于天地,渺沧海之一粟”的苍茫。蓝色封面的《尚书》,我第一次就翻到“功崇惟志,业广惟勤”这里,看到祖父他用钢笔在旁边添了句小字:“读书亦如是。”字体清秀,刚劲有力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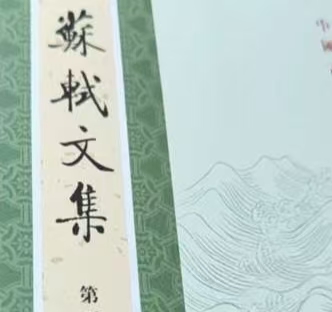
父亲说,他十七岁那年重复的看了《古文观止》,让我也在暑假里多看几次,尤其是一些精湛的句子,让我要像背功课一样背下来。于是,我也用心的在记,然后在写作上用进去,直到自己满意为止。读到《祭十二郎文》,我刹那间想起了我的祖父,不但是因为这其中的句子,却也因此而让我心里悲伤了起来,更让我想起了我的家族历史。

如今,我的作文本里夹着许多“文言习作”,虽然有的句子生硬得像小学生。但每次看到“克勤于邦,克俭于家”,或者是“以史为鉴,可以知兴替”,的句子时,总觉得那些铅字都活了过来。父亲大都是在晚上通过视频时看见我桌上的一堆作业,总是问:“今天看到哪里?写了什么?”我总是回答:“勿急,欲速则不达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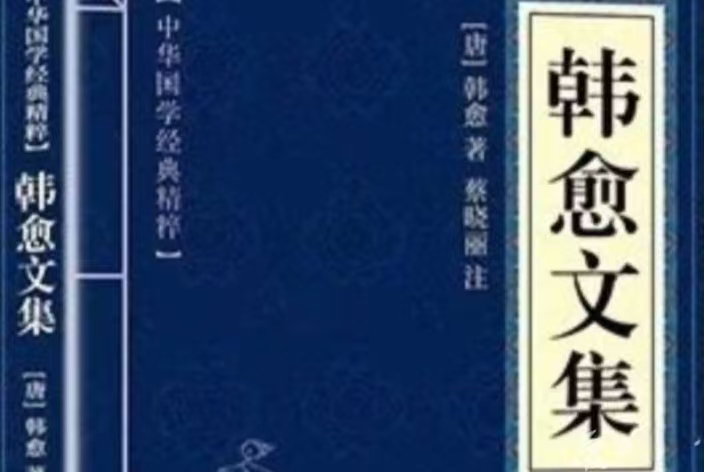
院子里的知了声时而响起,我却不再聒噪。我摸着书页上的折痕,忽然明白:古文不是博物馆里的展品,而是曾祖父、曾祖母、祖父的批注,还有父亲提起的那颗梧桐树,它们穿过岁月,在我重新翻开书页时,轻轻说了一声“原来你也在这里”。
附录:作者简介

徐仕扬
徐仕扬,男,汉族,2008年8月出生,祖籍为浙江嵊州,民国官员徐士达曾孙。徐仕扬自幼受祖父徐荣生启蒙教诲,更得父亲徐淇昉悉心教导,故深好古籍诗文,谦逊笃学,略有心得。虽为学子,然心慕先祖,愿承家学,以文述志。

